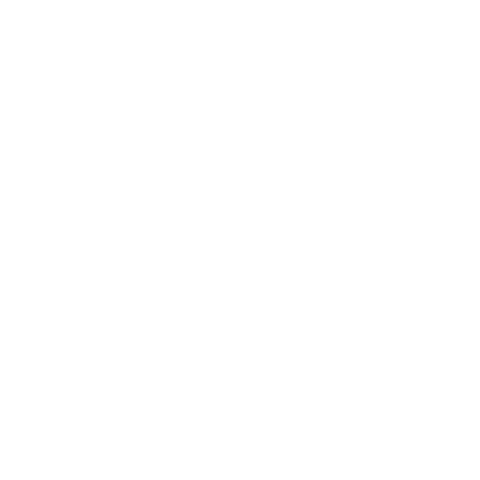内容提要
国际类器官鼻祖Hans Clevers,目前担任罗氏公司(Roche)药物研究与早期开发(pRED)主管,于近期接受了采访,讨论了类器官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的作用,相关对话发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
Hans Clevers总是被科学的空白领域所吸引。“人类有一种倾向,就是问一些你已经知道大部分答案的小问题,因为确认你的想法会让你感觉很舒服。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不是我们获得意外重大发现的方式。” Hans Clevers说,他从免疫学家转变为分子遗传学家,后来又转变为发育生物学家。“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迫使自己离开舒适区——进入我们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的领域。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实验系统,搅动它,看看会发生什么。”
通过这种“干扰和观察”的基础研究方法,Hans Clevers多年来在T细胞发育、肠道成熟和结肠癌方面获得了关键见解。然后,在2009年,他偶然发现了一种将干细胞转化为类器官(在试管中茁壮成长的“微型器官”)的方法,他的兴趣转向了转化研究。
“我们意识到这不仅是伟大的基础科学,而且还有很多应用,” Hans Clevers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通过生物技术和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他的学术实验室里探索类器官的机会——在药物筛选、疾病建模、临床试验设计和个性化医学方面。当他获得罗氏制药公司 pRED主管的职位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将这种类器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现在工作一年了,他对未来的挑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仅是类器官创新,而且是药物发现和开发过程的每一步。“我以为我知道药物开发有多复杂。它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Hans Clevers说。“它偶尔会起作用,这是一个奇迹。”他补充说,包括类器官在内的新兴技术有望提高成功的几率。
Q1
你对pRED中的类器官有什么看法?
在我加入罗氏之前,就已经在努力研究类器官对药物开发的意义。在pRED中,相当广泛地应用了人类类器官,基本上是小的人类器官用于安全性、毒性、药代动力学/药效学(PK/PD)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它分散在整个组织中,不是真正集中的。
我相信,人类的类器官最终会补充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整个药物开发过程是如何运行的,我确信我们可以在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运用人类类器官——从靶点识别和靶点验证,到安全性、毒性和PK/PD研究,再到临床试验中的分层,以及在个体化药物中作为预测个体患者反应的工具。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类器官需要得到很好的验证。“经过验证(validated)”是这里的一个关键词。许多关于如何使用类器官的想法并不新鲜,但它们还没有得到行业标准或监管机构的验证。这种验证只有在公司里才会发生。
但我梦想将类器官技术应用到pRED的药物开发管线中。我们正在围绕这一点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努力——与学术界紧密联系——你们将在几个月后听到更多。我希望通过这个即将到来的计划,更好地连接我们的科学家和学术界。
Q2
你说过类器官将“补充”其他方法。你如何预见类器官与细胞和动物模型共存?
我的感觉是,类器官最终会取代细胞系,因为你实际上可以将类器官标准化,让它们和细胞系生长周期一样长。我们用过的细胞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类器官也是如此,而且它们携带更多的信息。你可以个性化它们,你可以从10个不同的个体中构建10个不同的类器官库——例如,根据年龄、性别、种族背景精心挑选——然后将这些作为细胞系。
对于高通量筛选来说,这有点复杂。类器官不会在塑料上平面化生长,而且它们比细胞更难处理。但人们正在建立3D筛选试验——通常由基于图像的分析驱动,并由人工智能方法支持——可以从3D屏幕中提取比从2D屏幕中获得的更多信息。我把这称做“不费脑筋的事”。这是会发生的。
如前所述(这比我在pRED早),当没有其他模型用于安全性和毒性筛查时,类器官将被用作模型系统。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在一项试验性新药申请中,来自类器官或其他人体模型的大量数据,以及一个案例的所有数据。这可能会发生得更快。
但当然,制药科学还依赖于许多旧的检测方法,其中一些将很难被取代,因为它们是金标准。我们现在试着看看当把一个人类类器官模型放在金标准模型旁边会发生什么。它的预测效果好还是更好?这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东西,我们已经在积极追求了。
Q3
随着美国最近通过的一项新法律,FDA不再需要在新药试验开始前要求动物数据。动物福利组织欢呼这是一场胜利,但科学的进步是否足以让这项新法律产生很大的影响?
现在有许多简单、直接的安全测试可以在体外模型中进行。例如,在Ames试验中,用一种药物处理细菌,看它是否会引起DNA突变。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使用人类模型而不是细菌模型。这很简单。
但动物当然不只是一些简单器官的集合。类器官是对真实器官的抽象,而不是完美的复制。所以,如果一种化合物被给予动物,并在肝脏中代谢,然后在肠道和大脑中产生影响,这将很难用类器官来建模。你得在芯片上放上三个不同的器官,然后让它们朝正确的方向流动。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我们面对的都是复杂的生物体。我认为总有理由在真正的生物体中测试药物。
Q4
类器官体系如何使其模型更好?
现在的类器官只由器官的细胞组成,它们很好地模拟了这些细胞。但它们没有免疫系统,也没有血管或其他支持结构。目前,对于免疫介导疾病的良好模型,包括免疫性肿瘤,也包括炎症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尚未满足药物开发的巨大需求。我们目前对这些疾病状态的模型有很强的局限性,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构建更完整的器官——目前已经有很多努力在将免疫系统的元素植入类器官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疾病模型。
这将是该领域未来5-10年的重大任务。
另一件事是验证我们的试验,让高通量筛选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人员信服,这些检测是有用的。
Q5
更多的临床应用呢?比如将类器官作为细胞疗法或将患者纳入临床试验的工具。
我们发现类器官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培育器官并移植到病人身上,以解决一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但这非常困难。
各公司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最好地利用细胞疗法,而CAR - T细胞疗法可能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作为一个大型国际干细胞生物学家团体的一员,正在努力找出如何最好地应用所有这些见解来推进细胞疗法的使用。但是,最终,我认为使用生长因子——用来诱导干细胞变成类器官的蛋白质——将比使用类器官本身更容易。
随着我们对每个特定干细胞所需的生长因子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或许能够将这些见解转化为药物。但我认为我们不会在pRED中研究这个问题。
目前还在努力建立与ⅰ期和ⅱ期试验平行的类器官生物样本库。随着我们对这些试验中的患者进行跟踪,我们可以看到患者来源的类器官对其应答的预测效果有多好。现在的论文报告的预测准确率非常高,大约在85%到90%之间。在现实世界中,成功率可能会低于这个数字。这是我们目前在pRED还没有的东西,但我们希望能做到。
另一个应用是将基于类器官的药物敏感性检测用于个体化医疗(在真实世界环境中指导患者治疗)。
Q6
构建患者来源的类器官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有报道称,使用自动化和微流控技术,这可以在一周内完成。所以在治疗决策的背景下,这已经足够快了。
Q7
加入pRED后,还有哪些技术吸引了你?
我们活跃于两个被证明是困难的领域:基因疗法和基于寡核苷酸的疗法。我觉得这两者都非常有趣。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分子生物学培训时,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绘制出基因疗法的确切路径——这还需要3年的时间,每个人都将接受这些治疗。35年后,我们意识到这非常困难。基于寡核苷酸的治疗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反义和siRNA药物。
当然,我们的身体天生就能将外来基因信息拒之门外。这就是大自然的运作方式。这些领域的挑战是将基因和核酸传递到你想要它们去的组织。这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难题。但看到以前的尝试,我感到很兴奋,我们现在知道它可以在两个领域都有效。这些都是我们在罗氏公司重点关注的领域。
这些都是新的模式,而我们只是触及了如何使用它们的表面。
Q8
鉴于你对未知的兴趣,你认为你的科学好奇心会把你带回到更基础的研究问题上吗?
我想任何科学家都会意识到,当你研究一个特定的问题时,你会发现它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碰巧处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你阅读并与一些人交谈,你很快就会完全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这就发生在我身上。我发现这整个转化科学的挑战比我以前的生活更难以预测。在学术实验室里,你几乎可以控制一切,但偶尔还是会感到意外。药物开发越深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惊喜。我的注意力现在完全集中在这些巨大的智力挑战上。
参考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23-00030-y